|
作者:鲁舒天编辑:黄主任、戴老板来源:远川研究所(ID:caijingyanjiu) 全文字,预计阅读需16分钟。 在马保国跻身顶流之前,上一个通过非正常途径引发全网热度的,还是豆瓣4分职场剧担当——靳东。 靳东有万微博粉丝,但他之前挤上头条的时刻,大多跟他对都市精英的浮夸和土味演绎有关,如果不是不久前的“假靳东”事件,很多人恐怕想不到,真有不少观众会迷上他抖鸡汤时的西装革履和锃亮发胶。 比如家住江西、年过六旬的黄阿姨,她只知道自己一上抖音,这位英俊的中年男演员就会对她嘘寒问暖,还许诺给她一套房子和万。很少有人能给黄阿姨解释清楚:手机里的“靳东”不过是个AI合成的虚拟形象,是专门来骗她的。 不过在整件事中,最耐人寻味的其实不是拙劣的骗局,而是骗子们选择靳东来冒充的背后原因。 这帮收割者精准地绕开了易烊千玺、王一博、刘昊然等“国民弟弟”,转而匹配了与目标受众认知相符的非顶流艺人。换句话说,在以三四线以下城市中老年妇女为收割对象的骗局中,恪守男德、浓眉大眼、老干部形象的靳东才是正确答案[13]。 这就叫不选最贵的,只选最对的。 众所周知,北上广深和三四五线长久接受不同的信息内容和文化符号,由此形成迥异的审美趣味与消费习惯。在移动互联网进入下半场后,技术进步加速铺平传播渠道,在同一种媒介的覆盖下,城乡二元的文化割裂只会更加云泥两判。 在海派清口早无立锥之地的上海滩,李诞和笑果文化成为新的喜剧之王,一举成为流行符号No.1。可如果你打开最新一季的《脱口秀大会》,就不难明白脱口秀这项舶来品为什么只在一线城市风靡,却无法在更广袤的中国内陆落地: 颜怡、颜悦在婚姻段子里致敬库布里克的《闪灵》;杨笠在女权段子里调侃“漫威”黑寡妇的衰老速度比别人慢,杨蒙恩则在行业段子里插了一个历史梗:“我来参加脱口秀大会就像去了太平天国一样,遍地是大王,短暂又辉煌……” 很显然,理解这些梗,需要很强的文化积累才能get到笑点,这已然超越了国人平均文化水平的上限。这么一对比,何广智和李雪琴的地铁段子就比较接地气了——虽然每天都挤地铁的上班族,仍是一个只属于一二线城市的场景。 要说最不接地气的,是喜欢“飙洋文、秀优越”的Norah,这种更对留学生胃口的风格被李诞提醒“喜剧演员不要给人那么大的压迫感”。李诞的意思是:一个表演者不能放低姿态,就很难触及更广泛的共鸣,到头来是在自说自话。 李诞的文化经验来自张楚、布可夫斯基、马尔克斯和库斯图里卡,但他从不追求曲高和寡,而是选择不断降维降维再降维,原因也很简单:如果内容离最大公约数太远,别人干嘛要抢一票难求的小剧场,躺在床上刷抖音岂不快哉? 当然在今天,五环内精英再怎么降维,也很难继续向下穿透:五环外的人对五环内流行哪个艺人、哪部美剧、哪款应用一无所知,也没兴趣知道;五环内对五环外平日里玩什么、刷什么、跟什么大哥、做谁的家人,一样是毫无察觉。 昔日赵本山“穿个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”和赵丽蓉的“宫廷玉液酒,一百八一杯”这种能够穿透全国人们的梗,再也无法重现了。村村通网后,互联网上显露出来的文化割裂,可曰“北上广没有靳东,四五线没有李诞”。 所以问题来了:我们的物质生活在折叠,精神生活是不是也在折叠? 1 现象:文化折叠 年3月,一个湖南湘潭人有备而来地发表了一篇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,里面有这样一段话:“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,和在汉口、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到的道理,完全相反。许多奇事,则见所未见,闻所未闻[1]。” 这篇历时32天的田野调查,只是为了说明一点:于社会观察而言,想要得出正确认识,务必亲自去下面看一看,决不能闭门造车。 九十年后的一日,纪录片导演李一凡充分领会了革命导师的“认真”精神,为了搞清90后农村青年的生存状态,他去工厂流水线实地蹲点,与拍摄对象互加好友、同吃同住,终于拍到了在国内曾经风靡一时、却又销声匿迹的杀马特。 杀马特或许是一种信仰、态度或主张,但它首先是一种发型,特点是五颜六色又四面开花。在“45度角仰望星空”成为流行金句的那些年,杀家军三五成群地顶一脑袋在街上走,构成了泛城乡结合部最朋克的风景线。 有人看不惯,笑它“非主流、洗剪吹”,还有人直接批“脑残、低俗”。年之后,杀马特逐渐跟火星文、山寨混搭、仰角自拍等关联符号从主流视野中消失殆尽,以至于给拍摄者只闻其名,不见其人的印象。 经过不懈努力,李一凡通过线人混进了“葬爱”圈子,在东莞石排镇找到了最后的杀马特。 根据他的统计,杀马特成员几乎都是中小学辍学的留守儿童,进工厂平均年龄14岁,不懂社交、空虚寂寞、基本胆小,普遍抑郁,来到陌生人社会后,大多有被偷被骗的经历,有人一下火车站包就被拎走了。选择加入组织,是因为这层保护色看上去唬人,也便于相互建立认同[10]。 李一凡说,进入杀马特的世界后,他才发现这里“毫无精彩可言,只剩下流水线上的单调与疲劳”。那些被社会视为异端的夸张造型,不过是这些人仅剩的减压阀。可现在,杀马特只能在“污染市容、有伤风化”的谴责中剪去头发,重新到每15分钟换一班的工位上洗心革面,老实呆着。 《我拍了杀马特》的视频在一席出圈后,网友称其“杀马特的精神史”。但这部上映于年的片子其实是一部“迟到”的纪录,昔日超过万人的杀马特家族早已消失殆尽,导演能采访到的“活杀马特”数量,其实已经不足10个。 近年来最“及时”报道文化撕裂现象的,反而是一篇自媒体
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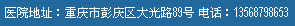 当前时间:
当前时间: